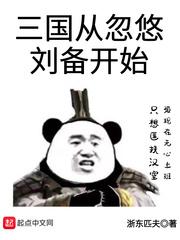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272章 271秦岭(第2页)
“嫩这后生胆子紧,黑队赶什么路。”待唐植桐进门,大爷又将大门关上,还不忘嘟囔一句。
“大爷,有柴房吗?我凑合一宿。”唐植桐放好自行车,也没心思猜大爷话里的意思,又打了个哈欠,问道。
“来这屋。右手边有个炕,嫩在这凑活一宿吧。”大爷也没二话,给唐植桐打开旁边偏房,灯都没点。
“好嘞,谢谢大爷。”唐植桐从兜里摸出火柴,划着一根,借着短暂的光亮坐在炕沿上,甩灭,然后先把五六半放在床头,也顾不上脏不脏,躺下就睡。
大爷给唐植桐带过门去,没回屋睡觉,而是摸着黑出了门。
一会的工夫,这大爷来到另一家人家门口拍门:“老憨开门!”
“张老汉儿,咋咧个嘛,乌漆嘛黑的叫门。”里面的人听到动静,出来房门,不满的嘟囔道。
“咋咧个?嫩家瓜娃子上报的那两只家伙,上面来人取了,嫩说怎么办吧!”张老汉没进屋,在院子里,掏出随身带的烟袋,挖上一锅烟丝,拿出火石擦两下打着,蹲在地上吸了起来。
“嫩咋知道?”老憨一听麻爪了,赶紧蹲下来问道。
“嫩睡的死嘛?刚额家狗叫的凶,找上门了。”张老汉没好气的回道。
“那可咋办!要不把皮交给人家?”老憨搓着手,也没个主意。
“县上说了,要活的。嫩瓜娃为啥自作主张上报?这玩意就不是个能养活的。”张老汉依旧没好气,埋怨老憨,也是埋怨县上,这玩意不好养,可偏偏县上不收过去,而是让村里养着,这不是难为人吗?
唐植桐没找错地方,这里就是沙家坪,老虎是老憨带儿子前几天抓住的,很不幸,太小,没养活,被队上扒皮分着吃了。
“那啷个办嘛,再去抓也没这么快嘛。”老憨蹲地上抓着头,一时也拿不出个主意。
“姥姥!明儿一晌开个会,那娃得睡到晌午。”张老汉也没有好办法,在地上磕磕烟袋,站起身来,转身往回走。
第二天一大早,小队里的几个主事人碰头开会,了解情况后,却一个个都借着抽烟不说话。
本来是想着报上去挣个先进、表扬,没成想县上立马表态说要活的!而且是四九城来人取!回来传着传着就成了献给那谁!
可偏偏两只小家伙前两天死了,拿不出来就是欺骗那谁,没人愿意承担这个罪名。
“都说说,咋咧个办?”张老汉起了个头,问道。
“要不,去响水岩走一遭?”有个汉子看没人说话,犹豫再三开口道。
“不要命咧?那可是虎王。”有人质疑,却也只是小声嘟囔,不敢大声嚷嚷。
“就响水岩咧,去一趟,掏不到就算球,爱咋滴咋滴!”张老汉深吸一口烟,拍了下桌子,一锤定音。
此时,唐植桐还在补觉,这一觉睡到了中午头才醒。
醒后揉揉眼,坐起来伸个懒腰,看看手表,已经十一点多。
手表不是自动上弦,唐植桐摘下来上弦,又戴好,才背着枪出门。
回到三国战五胡
这是东汉末年的时代,又不同于记忆中的那个东汉末年。当三国演义的撒豆成兵成了真,最强鲜卑,最强契丹,最强蒙古,最强女真,最强突厥,盘踞在汉室的塞北之地,对大汉疆域虎视眈眈。零散的召唤异族势力,更散布大汉边陲,谁说开局不利,就不能染指大好江山?金戈铁马的战场,热血沸腾的争霸,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主旋律,这里是属于最强者的时...
藏玉纳珠
玉若有魂,当如伊人。他隐身于庙堂之高,看得清天下,却看不清那看似卑贱的女人玉琢冰雕容貌下掩藏的真心。刃若有魄,当如斯人。她毕生的心愿不过是追求玉雕的极致技艺。奈何,这浮萍飘摇乱世,又怎么容得她这寄人篱下的下堂妇一朝成就匠魂之名?何况那个阴沉莫定的男人,倨傲地对她说若是牵住了我的手,就容不得你放开亲们久等了...
三国从忽悠刘备开始
汉灵帝西园租官,要不要租?租!当然租!因为只要恰好租到灵帝驾崩前的最后一个任期,就等于直接租房租成了房东!租官租成了诸侯!所以,匡扶汉室怎么能只靠埋头苦战...
小妻好甜:陆少引入怀
不要叫我后妈,我没你那么大的儿子!艾天晴一直以为自己要嫁的人是一个快六十的老头,直到某天晚上那个邪魅冷血的男人将她抵在了门上,从此她的日子就...
恐怖教室
学校后面有一个废弃教学楼,经常有人在里面失踪。但只要出来的人,都能一夜暴富。我偶然之间进去了,破旧的教学楼,昏暗的教室,还有一个穿着校服,手拿匕首,满身是血的女人。我出不来了...
强制婚约:总裁老公我不约
她本是叶家千金,因受继母算计,被迫流落在外。而他是景城的主宰者,权势滔天,杀伐果断。偏生,两人自小订了婚约,可他家人瞧不上她,逼迫她退婚。叶星辰潇洒挥手,没问题,这婚约,我本来也没想要。谁料,他霸气出场,壁咚她,女人,这婚约由不得你不要,既然是我未婚妻,没我同意,你敢取消?叶星辰表示,没什么不敢。谁知道,三言两语就被他拐去民政局领了证,盖了章。从此,她身上多了一个‘人妻’的标签。...